商榷与探索 | 刑民交叉视角下虚构工程量结算行为的法律评价与界分研究

主持人:王建东教授
“商榷与探索”栏目由本所创始人兼名誉主任王建东教授主持,围绕工程建设领域疑难复杂法律问题展开思考,诚邀各位“多出难题”,共同“破解难题”。
刑民交叉视角下虚构工程量结算行为
的法律评价与界分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二、实践中虚构工程量结算行为的表现及特点
三、虚构工程量结算行为的多重法律评价
四、刑民界分的理论探讨与实践争议
五、结论
一、问题的提出
在建设工程领域,工程量结算作为项目资金流转的核心环节,其真实性直接关乎市场秩序、工程质量与公共利益。近年来,“虚构工程量结算”行为频发,因行为性质横跨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模糊地带,司法实践中屡现“同案不同判”现象:同一虚构行为可能被民事法庭认定为可撤销的合同瑕疵,亦可能被刑事法庭定性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等犯罪。这种刑民界分的混乱,不仅削弱司法公信力,更导致市场主体合规预期模糊,阻碍建筑行业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厘清“虚构工程量结算”行为的刑民法律边界,成为理论深化与实务革新的双重命题。
二、实践中虚构工程量结算行为的表现及特点
(一)虚构工程量结算行为发生的环节
虚构工程量结算行为的发生贯穿工程项目的全生命周期,具有环节复杂、手段隐蔽、危害深远等特征。从行为发生的核心环节来看,主要集中于三个关键阶段:
1.招投标与合同签订阶段:在招标文件中的项目特征描述模糊、计量规则不明确,为后期结算争议埋下伏笔。利用不平衡报价策略,故意压低可计量项目的单价,抬高隐蔽工程或后期变更项目的单价。
2.施工实施阶段:利用工程变更、隐蔽工程验收等管理漏洞虚构施工内容;
3.竣工结算阶段:通过篡改施工记录、伪造签证文件等方式虚报工程量。
这三个环节形成完整的造假链条,且常呈现跨阶段联动的特点。
(二)虚构工程量结算行为的具体形式
在具体手段上,虚构工程量结算行为主要集中在以下五种典型模式:
其一为工程量虚增型,通过编造未实际完成的施工项目或夸大实际工程量套取资金;
其二为重复计算型,对同一工程部位在不同工序中多次计量;
其三为签证文件造假型,虚构设计变更或现场签证手续;
其四为隐蔽工程虚构型,利用地下工程、预埋构件等难以复核的特点虚报施工量;
其五为材料虚报型,在材料用量、规格参数等方面进行虚假申报。
这些行为往往依托工程管理的技术壁垒,借助专业术语和复杂计算规则进行包装,形成表面合规的虚假文件体系。
(三)虚构工程量结算行为的特点
1.技术隐蔽性,依托建筑专业知识和工程管理流程设计造假方案,非专业人员难以辨识;
2.主体多元性,常涉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多方共谋,形成利益共同体;
3.后果双重性,既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又可能因虚报工程质量引发安全隐患;
4.查处滞后性,因工程周期长、资料繁杂,违法行为常在竣工审计阶段甚至更晚才被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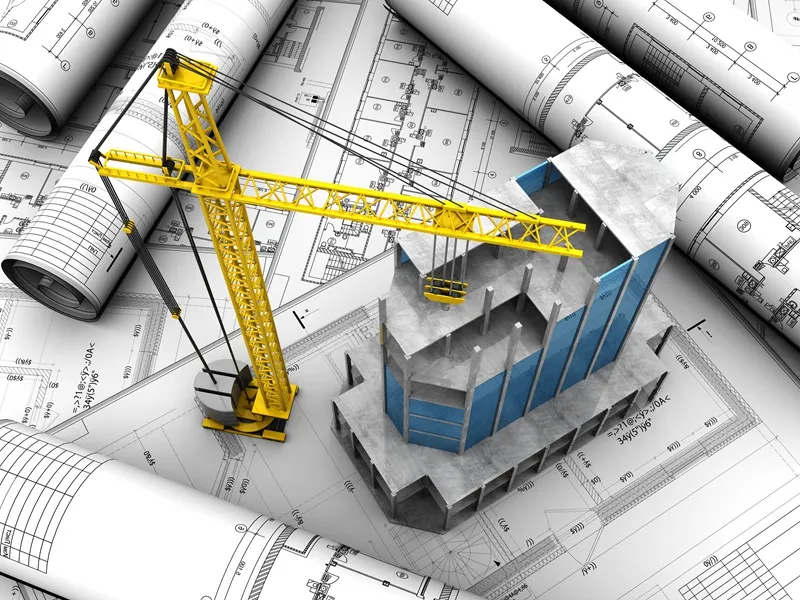
图源网络
三、虚构工程量结算行为的多重法律评价
从民事与刑事法律维度审视虚构工程量结算行为,其法律评价呈现多重性特征。

图源网络
(一)民事法律评价
在民事法律评价方面,民事欺诈可能是侵权行为也可能是违约行为:欺诈性民事侵权,是指行为人以欺骗行为造成他人权益受到损害;欺诈性违约,是指合同当事人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欺诈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并造成了实际损失。若虚构工程量结算行为系双方合意,如建设单位默许虚报以套取财政资金,则构成通谋虚伪表示,结算条款无效;若系单方“虚构”欺诈,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并作出违背真实意思的结算决定,受害方可主张撤销结算、返还不当得利、追究违约责任或请求赔偿损失。若虚构行为同时损害第三方利益(如金融机构贷款资金),可能触发债权人撤销权。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区分“技术误差”行为与“恶意虚报”行为,误差幅度在行业审价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不应当认定为“欺诈行为”。民事赔偿以填补损失为原则,虚报方需返还超额工程款并赔偿资金占用损失,但损失金额的确认不应当以行政评审结论直接替代司法裁判。
(二)刑事法律评价
在刑事法律评价方面,虚构工程量结算行为可能触发多项罪名的适用竞合。
1.诈骗类犯罪
(1)构成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实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如在(2019)赣01刑终425号熊伟光、万建平合同诈骗案中,行为人熊伟光作为施工方负责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华东建材城与嘉业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结伙采取虚构水塘淤泥外运,虚增施工范围外便道的签证单的方法,骗取建设方的财物。经法院审理认定行为人构成合同诈骗罪。
(2)构成诈骗罪
实践中,若虚构行为针对政府补助、保险理赔等非合同相对方,可能构成普通诈骗罪。如在(2020)浙07刑终377号徐小军、王跃武诈骗罪案中,时任武义县水碓后村党支部书记的徐小军,在明知村内道路拓宽工程未经审批的情况下接受应某1(道路拓宽实际出资人)请托,以水碓后村名义向武义县民政局申报“道路硬化工程”移民补助项目,虚构数据,骗取项目立项,并操纵招投标,在此工程中持有股份。其后徐小军通过结算审计虚增工程量,使案涉工程达到补助门槛,成功骗取武义县民政局下拨的20万元移民补助款,经法院审理认定构成诈骗罪。
2.构成职务犯罪
根据行为人身份、手段行为、侵害法益的不同,构成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不同罪名,主要涉及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直接或与他人串通套取公共资金,占为己有或挪作他用的情形。如(2019)湘08刑终134号吴悦贪污罪一案中,吴悦利用担任桑植县空壳树乡陈家坪村村书记、协助乡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职务便利,虚构工程量、伪造各种单据,将从扶贫责任单位张家界市发改委出资实施的项目中套取的资金119270元及桑植县公路局拨付的公路整修资金60000元占为己有,以涉嫌职务侵占罪被桑植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法院审理认定构成贪污罪。
3.构成伪造类犯罪
如通过伪造监理单位印章、审计报告等文件确认虚假工程量,可能构成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造价工程师、监理人员配合出具虚假结算报告可能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四、刑民界分的理论探讨与实践争议
如前所述,“虚构”工程量结算行为存在多元化的法律评价。民事法律侧重调整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失衡,刑事法律则以惩治严重法益侵害为目标,二者对“虚构”行为的定性标准如何衡量划分,理论与实务尚未达成统一观点与明确标准,以下对部分理论观点进行列明。
观点一:民事欺诈和刑事欺诈都以欺诈为其行为特征,民事欺诈可以分为民事违约的欺诈和民事侵权的欺诈;与之对应,刑事欺诈可以分为虚假陈述的欺诈犯罪和非法占有的刑事诈骗。对于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之间的区分,应当从欺骗内容、欺骗程度和非法占有目的这三个方面进行界分,从而为正确地认定刑事欺诈犯罪提供刑法教义学的根据。
观点二: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限关键在于:
一是看行为是否发生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民事欺诈是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发生的,这种民事法律行为可能因为诈骗而部分或者全部无效;诈骗罪虽然可以引起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但不产生民事法律关系。
二是看行为人实施该行为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诈骗罪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种主观目的在客观上通常表现为行为人通过虚构事实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财物,从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民事欺诈是通过夸大事实等诈骗行为而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进行对自己不利而对诈骗行为人有利的行为,其本质是不法获利。
三是看客观上有无虚构主要事实。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客观上都有欺骗行为,但二者在本质上存在不同。诈骗罪行为人虚构的是主要事实,是决定被骗方作出判断的主要依据,被骗方交出财物的行为是建立在完全虚假的事实基础上,而民事欺诈中行为人只是虚构了辅助事实,不足以影响被骗者的判断能力从而作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交付财物的决定。
观点三:在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时,应考虑“意思自治”是否被彻底击穿。简言之,在合同领域,意思自治与合同自由属于处理纠纷的基本原则,当事人基于合同约定解决纠纷。根据刑法补充性原则,只要通过民法领域的意思自治能够解决问题,就不需要刑法的介入;如果成立刑事诈骗,则一定是在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无法处理的场合,换言之,“意思自治”被彻底击穿。对于诈骗罪需采取限缩解释行为路径,将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核,即民事救济可能的基本丧失,纳入欺骗行为的认定中,以此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行为人针对“财产给付的基础事实”“民事救济的重要事实”进行虚构、隐瞒,导致被害人陷入失去民事救济可能的高度风险的行为属于刑法上的欺骗行为,构成诈骗罪。
在实践中,除前文构罪案例列举外,也存在相当一部分对行为人“欺诈”行为不予认定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例。如黄某正等合同诈骗案,行为人黄某正以临川一建的名义承包德恒公司某社区土建工程,以伪造签证单、虚构工程量方式获取超额工程款,经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其夸大数量的欺骗行为对合同最终适当、全面的履行不具有根本影响,不属于诈骗类犯罪所要求的根本上的“虚构事实”,不构成犯罪。
宣判后,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原审被告人黄某正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目的,客观上实施了在工程量签证单上虚增数量的欺骗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中“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情形,事后能否通过民事救济手段挽回损失,不影响合同诈骗罪性质的认定。九江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抗诉意见正确,支持抗诉。
二审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被告人黄某正、周某、袁某庆在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虽有虚增混凝土用量218立方米的行为,但综合全案情况及本案建设工程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不能认定黄某正等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虚增砼用量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不构成合同诈骗罪。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与在卷证据和查明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五、结论
笔者对现有理论及司法实践观点进行归纳梳理,认为对于“虚构工程量结算”行为的民刑分界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主观上,考察区分非法占有目的与履约意图
刑事诈骗:非法占有目的贯穿行为全过程,以完全占有他人财物为终极目标,行为人自始无履行意愿(如签订合同时即计划卷款潜逃)。
民事欺诈:欺诈动机与履约意愿并存,追求合同履行中的超额利益,欺诈行为服务于合同目的(如夸大履约能力获取订单,但确有履约意图)。
(二)客观行为上,考察欺骗手段与合同关联度、行为人履约的完整性
刑事诈骗:欺骗构成合同成立的决定性因素,虚构核心履约能力(如无施工资质的空壳公司承包工程),或仅象征性履行合同义务。
民事欺诈:欺骗仅影响合同部分条款(如虚报单项材料成本,但整体施工方案真实),具备基础履约能力,主要合同义务已实际履行。
(三)考察财产处置情况与损失挽回可能
刑事诈骗:资金用于个人挥霍、偿还非法债务,造成不可逆财产灭失。
民事欺诈:资金投入生产经营或继续履行合同,损失可通过民事救济恢复。
(四)考察权利义务均衡程度
刑事诈骗: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如收取全款后仅完成10%工程量)。
民事欺诈:存在实质对价关系(虚增20%工程量但完成合同主要义务)。
作者简介
赵烨律师
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浙江省法学会工程建设法学研究会理事
浙江省律师协会文化传媒与体育专业委员会委员


